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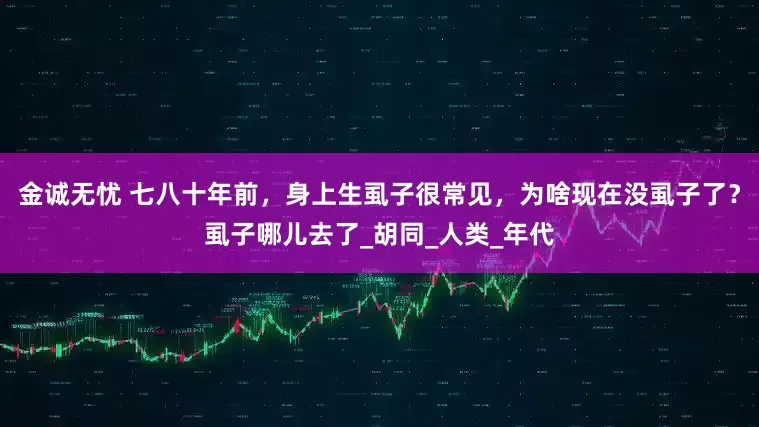
北京胡同里的老人常说:"谁家还没跟虱子干过仗?" 这话搁在七八十年代,能让半条街的人点头称是。那会儿街坊邻居凑一块儿,除了唠家常,就是互相给孩子篦虱子 —— 小姑娘的麻花辫一解开,发根上密密麻麻的小白点,跟撒了把芝麻似的,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姐小时候总喊 "妈!头皮痒死了",我妈举着煤油灯一照,气得直拍大腿:"这虮子都能凑两盘菜了!"
可邪门的是,这曾经 "家家必备" 的虱子,咋就跟突然人间蒸发了似的?现在的 00 后听长辈说 "用篦子刮虱子",都以为是神话故事。今儿咱就用胡同里的大白话聊聊这事儿 —— 虱子这玩意儿到底多顽固?当年人为了除虱有多拼?它又是咋被现代社会 "赶尽杀绝" 的?这里头的故事,比老北京的胡同名儿还绕。
一、虱子:人类身上的 "老住户",比祖宗还资深的寄生虫
展开剩余87%要说虱子这东西,那可是人类进化史上的 "钉子户"。科学家说它们在地球上蹦跶了 2.3 亿年,比恐龙灭绝还早 6000 万年。人类祖先还浑身是毛的时候,它们就已经在毛囊里安营扎寨了;等咱们祖宗慢慢褪了体毛,这货居然还玩起了 "兵种分化",愣是搞出三支 "吸血部队":
头虱:潜伏在头发丝里,专挑头皮毛细血管下手,白天躲着,晚上出来 "开饭",能把人痒得直挠墙,后脑勺都能挠出红疙瘩。那会儿孩子上课总走神,十有八九是这货在捣乱。 体虱:藏在衣缝裤脚里,尤其爱躲在棉袄的棉花里,跟住四合院似的。半夜爬到皮肤上吸血,让人睡得好好的突然蹦起来抓痒,跟中了邪似的。我爷爷的棉袄从立冬穿到清明,衣缝里的虱子能开运动会,一抖衣服 "噼里啪啦" 掉一地,比炒豆子还热闹。 阴虱:这玩意儿更刁钻,专往私密地方钻,爪子跟小钳子似的,扒得比 502 胶水还牢,抓都抓不下来。那会儿人不好意思说,只能偷偷用偏方治,遭的罪可不少。这三种虱子不光让人痒得难受,繁殖能力还强得离谱。一只母虱子一天能下 4-5 个卵,7 天就能孵出小虱子,三周就能凑齐 "祖孙三代",在你头发里开家族聚会。最绝的是,虱卵(就是咱说的虮子)能分泌强力胶水,牢牢粘在头发或衣服上,普通梳洗根本奈何不了 —— 就像胡同里贴小广告的,你刮一层,底下还粘着三层。
不过这货也不是一点用没有,科学家通过研究虱子的分化时间,居然算出了人类祖先褪体毛的年代。就冲这,也算是为人类进化史立了一功,虽然这功劳听着有点膈应。
二、七八十年代的 "虱子盛世":物资匮乏造出来的 "虫灾"
七八十年代的虱子为啥这么猖獗?说来说去,还是那会儿日子太穷,给虱子创造了 "安居乐业" 的好条件。1980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城镇居民一年平均才用 2.5 块肥皂,农村更惨,才 0.8 块 —— 这点肥皂,洗两件衣服就没了,哪够洗澡洗衣裳?
这直接造成了三个 "虱子温床":
一是洗澡跟过年似的金贵。北方家庭冬天洗澡,那得看黄历。胡同里的澡堂子冬天人挤人,进去跟下饺子似的,普通人家一个月能去一回就不错了。有那讲究点的,在家烧点热水擦身子,可哪有淋浴洗得干净?我奶奶常说:"从立冬到腊月廿八,身子骨都快腌出咸菜味儿了,虱子能不喜欢?"
二是衣服少得可怜,换都没得换。那会儿人均内衣才 1.5 套,洗了得晾三四天才能干 —— 说白了,大多数人就一套内衣,穿脏了也得硬扛着。我爸年轻时在工厂上班,夏天的背心能拧出黑水,领口磨得发亮,衣缝里的虱子比线头还多。更别说棉袄棉裤了,从冬天穿到开春,胳肢窝都磨出包浆,虱子在里头搭窝筑巢,过得比人还舒坦。
三是被褥跟 "虱子公寓" 似的。那会儿棉被芯几年不拆洗,棉花板结得跟石头似的,里头藏的虱子能编一个加强连。我家那床老棉被,我妈说拆的时候 "抖落出半斤灰,还有一把虱子",吓得我三天没敢盖被子。
除了物资匮乏,那会儿的居住环境也给虱子帮了大忙。上海石库门 "72 家房客",16 平米的屋子住祖孙三代,晚上睡觉挤得跟沙丁鱼似的,虱子在人身上串门比走亲戚还方便。农村更别提了,一大家子挤在土炕上,虱子从爷爷身上爬到孙子头上,跟走平道似的。
最要命的是学校,简直是虱子的 "批发市场"。1985 年报纸报道,河南有个小学爆发 "头虱疫情",600 个学生几乎全中招,老师没办法,在操场摆开 "梳虱流水线",一排孩子低着头,老师拿着篦子挨个刮,地上落的虱子能扫一簸箕。我上学那会儿,同桌总偷偷挠头,有次他甩头发,居然掉我本子上一只虱子,吓得我哭着找老师 —— 现在想起来,还起鸡皮疙瘩。
三、人虱大战的 "土法科技":当年为了除虱,多离谱的招都敢试
面对泛滥的虱子,那会儿的人脑洞大开,发明了一堆 "除虱神操作",现在听着都觉得魔幻。
最常用的是物理攻击:首当其冲是篦子,那玩意儿齿密得跟渔网似的,刮起虱子来 "噼啪" 响,刮完一看,篦子上密密麻麻的,有活蹦乱跳的虱子,还有芝麻粒似的虮子。我妈总说:"刮下来的够喂鸡了。" 除了篦子,还有 "开水烫"—— 把衣服扔开水里煮,虽然能杀死虱子,但衣服也煮得变形;冬天还有 "冻虱子" 的招,把被褥扔院里冻一宿,说是能冻死虱子,结果第二天发现,这货抗冻得很,照样活得欢实。
化学武器更是五花八门:那会儿最流行的是六六六粉,撒在被褥里,据说能药死虱子。可这玩意儿有毒啊,闻着就呛人,有回我爸撒多了,半夜咳嗽得直坐起来。还有人用煤油抹头发,说是能闷死虱子,结果弄得头发油乎乎的,招了一脑袋灰,还差点把枕头点着了。
更邪乎的是各种 "民间偏方"。陕西农村有大妈用朝天椒煮水浇头,说 "辣得虱子直蹦迪",结果把头皮辣得通红,痒得更厉害了;东北有工人用柴油涂内衣,说是虱子怕油,结果皮肤溃烂,差点感染;还有那狠人,直接用开水浇头,想把虱子烫死,结果把自己烫得掉皮 —— 现在看来是瞎折腾,但那会儿是真没办法,被逼得急了,啥招都敢试。
可这些招儿顶多能暂时缓解,想彻底除根难如登天。1983 年寄生虫研究所报告说,那会儿的虱子对主流杀虫剂的耐药性已经达到 67%—— 说白了,这货跟胡同里的 "老油条" 似的,啥场面没见过?普通招数根本镇不住。
四、虱子的 "灭绝之路":洗衣机和肥皂,比杀虫剂管用百倍
谁也没想到,曾经让人头疼的虱子,居然在短短几十年里销声匿迹了。这可不是虱子良心发现,而是现代社会的 "降维打击",把它们的生存空间彻底端了。
首功得归 "卫生革命"。90 年代以后,洗衣机跟肥皂慢慢普及了,这可比啥杀虫剂都管用。1995 年城镇洗衣机普及率突破 48%,60℃的热水一煮,虱子和虮子根本扛不住,连它们赖以为生的 "胶水" 都能煮化了。再加上洗衣粉、消毒液轮番上阵,虱子的 "防御工事" 瞬间瓦解。
洗澡也不再是奢侈事了。城市里家家户户装了热水器,冬天想洗澡随时能洗,农村的澡堂子也多了起来,别说一个月洗一次,一周洗三次都不叫事儿。我妈总说:"以前洗澡跟过年似的,现在天天能洗,身上光溜得很,虱子想落脚都难。"
衣服多了,虱子没地方去了。现在人均一年买 7.4 件衣服,内衣换得勤,脏衣服当天就洗,虱子还没来得及 "搬家",就被冲进下水道了。不像以前,一件衣服穿到包浆,给了虱子充足的繁殖时间。快时尚的兴起,更是断了虱子的 "口粮"—— 衣服更新换代快,旧衣服直接扔,虱子连传宗接代的机会都没了。
居住条件改善也帮了大忙。2000 年以后,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10.3 平米,独门独户越来越多,不像以前 "72 家房客" 挤在一起。独立衣柜、独立阳台成了标配,衣服分开存放,虱子想串门都没机会。阳光能照进屋里,被褥经常晾晒,高温一烤,虱子根本活不了。
就连宠物都帮了忙。以前农村的猫狗浑身是虱子,一蹭人就传过来了;现在城里人养宠物,洗澡比人还勤,驱虫项圈、除虱药轮番上,宠物身上干干净净,虱子想通过动物 "搭便车" 都难。
五、虱子没了,可那些日子还在
现在偶尔在博物馆见到篦子,年轻人都不知道是啥,得听讲解员说 "这是以前刮虱子用的",才恍然大悟。可在老一辈眼里,那玩意儿藏着太多回忆 —— 有半夜挠痒的烦躁,有母亲篦头时的唠叨,有同学间互相打趣的玩笑,还有物资匮乏年代的无奈。
其实虱子的消失,说到底是日子过好了。从肥皂短缺到洗衣机普及,从一家一套衣服到年年添新衣,从挤四合院到住单元楼,这些变化不光赶走了虱子,更改变了咱的生活。就像胡同里的王大爷说的:"以前愁虱子多,现在愁衣服多了没地方放,这日子,真是翻着跟头往上走啊。"
当然了,虱子也没完全灭绝。听说非洲贫民窟和印度农村,还有 20% 的孩子头上有虱子 —— 这提醒咱,好日子来得不容易,得懂得珍惜。下次再看到篦子,不妨想想:这玩意儿不光是个老物件,更是把尺子,量出了咱生活的进步。
最后说句实在的,虽然虱子让人头皮发麻,但没了它们,还真有点想念那些 "边篦虱子边唠嗑" 的日子。毕竟,那是一代人的童年,苦是苦了点,可透着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,不是吗?
发布于:江西省诚利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